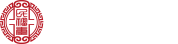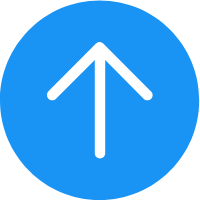中医寻根文化 孔子学说和中医的关联
《关注》一文认为,“作为医家经典,岐伯第一句话论‘道’不论‘病’,首先表明的是健康长寿的途径和目标:知‘道’且合于‘道’。这是中、西医学起点和着力点上的差异:‘健康医学’还是‘疾病医学’;‘防患于未然’还是‘渴而穿井’”。其实,如果真的只是有“道”而没有治病的实践和学问,自然也不可能去论“病”,不去论病的防治,又如何论健康?所谓健康与疾病是矛盾的两个反面,没有疾病,也就无所谓健康。人类医学实践过程是从有了病而开始的,而不是从健康开始的。假如有了人类而没有病,就没有医学,也就没有什么“健康医学”。医不能以健康界定为学。例如现在大家都在说的“治未病”,并不是“不论‘病’”。因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必须首先明白肝病、脾病及其两者的关系,“不论‘病’”,只“论‘道’”怎么行?“治未病”,首先要明白“治未(何种的)病”,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治”。
因为儒家文化偏属于道德哲学,他们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缺乏科学创新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受此影响中国传统科学的经典著作,多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或经验总结,而对这些自然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则探讨较少。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击的是标新立异。在孔子的心目中,如《关注》一文所言,“经典一旦出现就是无与伦比、难以跨越的,她已道尽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正是这种读‘经’经验,历代‘大家’才会走一条先是‘六经注我’、后来‘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子。‘六经注我’是指引经据典表达‘我’的观点;‘我注六经’是指后来发现‘我’的观点其实圣人已经讲过,且寓意深远,只不过点到即止。我的任务就是阐述一下让世人更容易读懂一些而已。‘我的述’仅是一条途径,经典才是终点”。《关注》一文还说,“研习《伤寒》到一定程度必读《内经》,研习《内经》到一定程度必读易、老;那么,在读易、老、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必读孔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关于伤寒“六经”的实质,关于仲景言阴阳不及五行,关于寒温的统一等问题,众说纷纭,皆从《内经》引经据典,却不曾见有统一;“读易、老”更解决不了问题。“经典才是终点”,岂不是说中医科学是“在倒退中前进”?这完全是一个自毁命题。
我们不禁要问:中医的学问就是在这几本“经典”之间“注”来“注”去吗?如果在读孔子时又遇到“发展瓶颈”了又该如何呢?《关注》一文也说了,西方科学不断出现“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的旧理论被淘汰和新理论诞生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同的文化影响了不同的科学精神。从科学史也可以看出,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会创立“日心说”吗?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吗?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相对论吗?他们虽然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认为科学是“可错的”,这才会有进步。这与亚圣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倒是不谋而合。我国当代的科学发展观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充分认识了“经典”与“现代”均具有两面性,而且是可以互补的;中医学的前途已不言自明,这就是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绝不是如《关注》一文所言的“经典才是终点”。
让中医理论之树常青
中医学只有具有开放系统的创新本质和趋于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种“不受西医学影响”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中医学术的传统文化基因缺乏自信的表现。
歌德在《浮士德》中有句名言“一切理论是灰色的,唯生活之金树长青”。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的认识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对中医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起了一定的支架作用,作为价值观对于中医伦理学起了奠基作用。但是医学理论之树,不可能脱离医疗实践而产生,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发展。例如老子极力主张倒退到一个“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社会去,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在他替圣人苦心设计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国里,国家小,人口稀,虽有舟车,没有必要去乘坐;虽有铠甲兵器,没有必要把它摆出来。人们过着“不织而衣,不耕而食”的生活。这与前述西方的文化寻根主义的人类学家的主张又有相似之处。诚然,如果地球上的人类再一次被天灾或人祸所重创,也有可能重新回到“纯绿色低碳”的“侏罗纪”时代;但现在看,还不至于在近年内发生。例如我国现有人口至少十三亿,你就要按十三亿人的要求去解决衣、食、住、行及看病难等问题。如果只是论“道”而不论“病”,不仅是脱离现实,而且是不人道的。
《关注》一文说“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这一比喻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医这“一棵树”是怎么来的。中医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古代,既无圣贤,又无经典的时候,就有了人的疾病和驱除疾病的实践。例如在已出土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许多关于疾病(三十几种)与人体解剖和功能的记载。也就是说是先有了病和治病的砭石或药、酒甚至手术,之后才有了理论。实践才是理论的渊源。而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被大量借用,即原本不是中医固有的理论和方法,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一元论、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取象比类等被大量引用借鉴,将无数人的实践结晶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不但成就了中医理论的完整体系,还直接代替和弥补了实际医学知识的不足;古人将实际对象中发现的原形,与哲学思维模型结合成了亦虚亦实的中医理论。也就是说,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不是由黄帝或希波克拉底的“第一次推动”而运转起来的“永动机”,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数人实践信息的反馈系统。其发展的动力来源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其理论体系和学术特征及知识范围都必然以实践为依据而与时俱进,这就是中医学的发展规律。
所谓“阳光”、“空气”、“土壤和水”都是中医学之树的生长环境,不是千年不变的“经典”。“经典”早已注入大树的基因中。医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第二性的,它的发展虽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却不能以固有的理论特色为必须遵循的“规律”,因为它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受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研究实践的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的。所谓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也不存在现代化不现代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把中医发展规律与中医固有理论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学术研究应当追求系统的开放、理论的交叉,信息的交流、方法的互补。中医研究的创新性与开放性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味地提倡所谓“独立自主”。医药学的发展总是后人超越前人,中医学只有具有开放系统的创新本质和趋于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